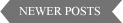考前幾天午晚膳食皆由媽準備。我們站在一張側對教室門口的長椅前吃飯,就是那時遇見水果爺爺的。
約莫用餐前一刻鐘,水果爺爺便提一臺鹽紙袋蹣跚而至。深紅基底,白色格紋的襯衫,外罩一件老式樣但是上好質料的茶色開襟毛衣,配上灰色西褲與略微磨損的棕色皮鞋。這是他的制式服裝。
某天媽忍不住,於我未下課前去和他攀談。原來是替孫女送水果的。應是名退休公務員吧,媽說。「說話非常有禮。」
那天我提早下課,站在空蕩蕩的廊上扒著便當。水果爺爺緩緩走來,將臺鹽紙袋擱在一處,凝望深鎖的教室大門。
媽走上前。「爺爺,又來送水果啦?」水果爺爺轉過身,一面客氣地向我們鞠45度的躬,一面以字正腔圓的北京話「是阿,是阿」說著。寒暄兩三句,水果爺爺生怕打擾母子談話似的,向我們點個頭便踱至那面貼滿高分作文之牆,取下眼鏡扶壁漫看。
鐘聲響。用完餐整理食具的我瞥見水果爺爺不知何時手上已拎著那只提袋,面對大門穩穩立著。媽喚我回房取待洗衣物予她,我只是嗯嗯阿阿含糊以對。
我究竟在幹嘛?
我在等大門開啟,水果爺爺的孫女走出來的那一刻。她會是怎麼樣的人呢?也許是俐落綁著馬尾,兩頰多了一點肉的豐滿女孩。穿著鵝黃色T恤、深色牛仔褲和粉色娃娃鞋的馬尾豐滿女孩,我想。
媽納悶著為何我遲遲不上樓,急了性子多嘮叨幾句。我試圖將應聲、回頭、起步三動作中夾雜刻意營之的心不在焉。
在我尚未別過身邁步前,孫女始終沒出現。
只是水果爺爺自我視線消失前的那副光景我猶記憶深刻:起了一陣戲劇性的風,一些紙屑之類劃著不存在的圓心戲劇性地轉。那牆作文戲劇性地騷動著。取午餐的同學戲劇性地瞇起了眼。甚至,在我記憶中,那變成了一道旋風一般強勁的力道,在短短30秒內掃遍大樓每處角落。
唯獨水果爺爺站得直挺挺的,閱兵似的挺立。紋風不動。
rest
關於Dizzybaron
嘀嘀咕咕.
Photostream
Blog Archive
MENU
Yawn Copyright (c) 2011, All Rights Reserved. Design by Dzignine
&
Pixel Oplosan
Proudly Powered by Blogger (of course)
Proudly Powered by Blogger (of course)